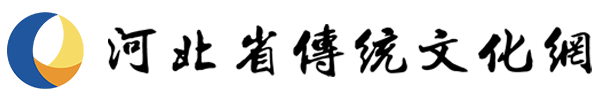笔铸丹心,文架桥梁——中国红刊传媒创始人黄光宇的写作心路

红刊杂志社编辑部电(孙业腾)在澳门郑家大屋的青砖黛瓦下,一面五星红旗的鲜红格外醒目。《中国新闻发布杂志》特邀策划(编辑)、中国红刊传媒创始人黄光宇凝视着这抹色彩,指尖拂过《红刊》创刊号的封面——正是这青砖与红旗的碰撞,开启了他以文字为媒、传承红色基因的写作之路。

初心:红色基因的澳门回响
我的写作初心,早已刻在童年的故事里。出生于红色革命家庭,祖父口中湘江战役炊事班长用铁锅当钢盔的事迹,如同种子般在我心中扎根。2021年移居澳门后,这片中西交融的土地既让我沉醉于多元文化的魅力,更让我陷入深思:濠江中学老校长杜岚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壮举,叶挺故居里藏着的革命印记,这些珍贵的红色记忆竟多散落在历史的角落,鲜为青少年知晓 。
“澳门需要一本能系统讲述红色故事的刊物。”这个念头彻夜萦绕。彼时的澳门虽洋溢着爱国爱澳的氛围,却缺乏专门的红色文化传播载体。我意识到,写作不应是空洞的口号,而应是对本土历史的深刻挖掘——唯有让红色故事接上澳门的“地气”,才能真正走进人心。创办《红刊》的决心就此笃定,而“讲好中国故事,传播好中国声音”的使命,也成为我此后所有写作的核心罗盘。
实践:在守正中寻找共鸣密码
创刊初期的写作探索,是一场“历史与当下的对话”。我为团队定下“三真原则”:真实的故事、真挚的情感、真切的共鸣。为了挖掘“红色记忆·澳门印记”专栏素材,我们走访26位澳门老居民,在82岁符老先生珍藏的《新民主主义论》泛黄扉页中,触摸到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。这些口述史料化作文字,让读者看到澳门并非红色文化的“孤岛”,而是中国革命史的重要一页。
写作最怕“自说自话”,如何让红色文化既“保真”又“动人”,是我反复琢磨的课题。我们开创“大历史、小切口”的叙事方式:解读澳门施政报告时,不用官样文章,而是聚焦政策背后的民生温度;讲述革命历史时,不局限于宏大叙事,转而记录普通人的家国情怀。当《红刊》转载冼星海《黄河大合唱》手稿影印复印件后,一位澳门青年读者的来信让我备受触动:“原来民族精神早已融入先辈的创作血脉。”这让我更加确信,写作的真谛,是用可感可知的故事搭建情感桥梁。
突破:技术赋能下的传播革新
时代在变,写作的载体与形式必须与时俱进。我逐渐意识到,文字表述所涵盖的传播表达不是终点,而是红色文化国际传播的有力起点。在“内容创新、技术赋能”的四维格局指引下,我们开始探索“文字+”的融合写作模式。
在“青年新征程”专栏中,我们不再满足于人物专访的传统写法,而是搭配AI互动课堂脚本——当文字描述的叶挺故居,通过VR技术变成可“走进”的场景,当史料中的红军战士,能通过人工智能与青少年“对话”,文字便有了立体的生命力。2023年“红刊抒濠情”书画展的文案创作中,我们将6幅10米长的长征主题画作转化为文字故事,让艺术与文字相互赋能,吸引3万澳门市民观展,这正是跨媒介写作的力量。
写作更要打破语言壁垒。我们推出中葡双语版《红刊》,在“可亲可敬的中国故事”专栏中,用葡语读者熟悉的叙事逻辑讲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。当6000多套葡文版丛书通过中葡论坛送往葡语国家,当“红刊会客厅”的访谈在脸书、Instagram引发热议,我看到文字跨越国界的可能——写作既要保持中国底色,更要学会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说话。
远行:从澳门窗口到国际舞台
四年笔耕不辍,《红刊》已发行二十余期,但我的写作心路仍在延伸。2025年在马来西亚设立首个海外编辑部时,一位汉学家的话让我铭记至今:“你们正在做的,是让世界读懂中国精神的伟大事业。”这句话更坚定了我“立足澳门、背靠祖国、面向世界”的写作方向。
如今,我的写作计划里,既有“大湾区红色文化数字资源库”的文字注解,也有与中国传媒大学合作的《龙虎门》红色短剧IP脚本;既包含“敦煌艺术与红色文化联展”的国际传播文案,也涵盖“国史进校园”的青少年读本编写。这些写作实践始终围绕一个核心:让红色文化从“静态展示”变为“动态体验”,从“澳门叙事”升级为“国际表达”。
站在濠江之畔回望,从创刊号上那抹青砖与红旗的配色,到如今多语种、跨媒介的传播矩阵,我的写作心路始终与“文化润澳”“国际传播”的时代命题同频共振。正如我常对团队说的:“写作既是记录者,更是建设者。”未来,我仍将以笔为犁,在红色文化的沃土上深耕,让文字成为连接澳门与祖国、中国与世界的精神桥梁。
编审:刘鑫闻 王正义
责任编辑:孙业腾 赵道远
版权声明:本作品著作权归红刊杂志社独家所有,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。
文章来源:红刊杂志社